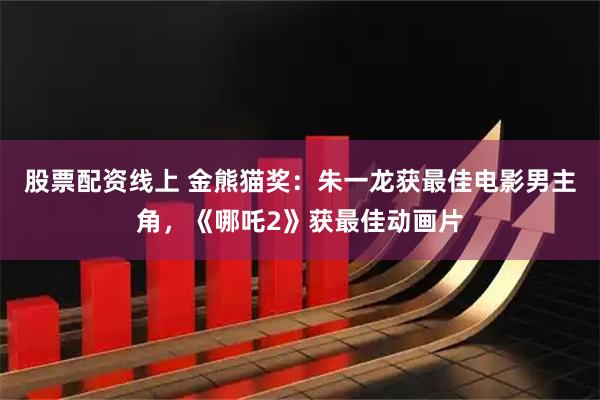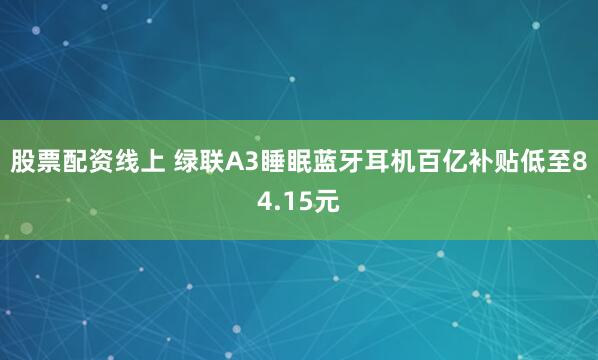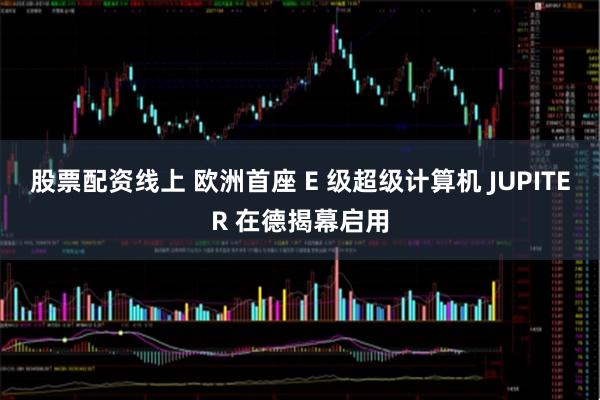印人党已经进入政治衰退周期。过去十多年,该党通过话语塑造、多数主义身份构建和福利分发支撑其在印度的支配地位。然而,印人党的政治霸权正遭遇系统性挑战。印度教民族主义提供的情感价值逐渐无法弥补物质改善的乏力。“全球崛起”的政治话语因印巴冲突与美印摩擦受到削弱。反对派恢复信心,联盟内部协调性增强,在议会监督及选举诚信等关键议题上形成实质性制衡。在此背景下股票配资线上,印人党试图通过强化对选举委员会的控制及操纵选民名册来维持优势,但此举反而揭露了其合法性焦虑。

印人党在选举中依然保持强势,但其政治霸权出现疲软态势,叙事能力减弱,而反对派的信心不断增强。在过去十多年里,印人党不仅主导了印度政治,还重塑了它。该党直接管辖15个邦及联邦辖区,并在另外6个邦与盟友共同掌权。即便在未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借助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发挥重大影响。其崛起依托于文化进取心、制度支配与强硬的民族主义有机结合,营造出“不可战胜”的氛围。然而,这一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尽管印人党在选举上仍具备强大竞争力,但在塑造社会认知、主导公共话语以及压制反对派方面的能力开始出现裂痕。近期趋势显示,印人党曾经不可撼动的地位正面临十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印人党的政治议程长期围绕“印度教特性”、民族自豪感及多数派身份构建,这一策略掩盖了经济政策表现不佳、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少数寡头对公共政策施加过度影响的现实。印度教特性的情感受益曾替代物质改善。然而,这种均衡正逐渐失效。青年失业率高企,工资增长停滞,非正规部门仍在应对废钞令、新冠疫情及商品与服务税的影响。对于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来说,就业机会与向上流动的承诺超过象征性政治胜利的吸引力。在话语与现实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中,印人党的叙事霸权开始动摇。
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不仅源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动员效应,还根植于对国际认可的承诺:印度在莫迪总理领导下跻身“受全球尊重的大国”之列。外交可见度的提升,高规格峰会的举办,以及精心塑造的“国际地位”形象一度被视为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这一叙事的动能正在减弱。尤其是在帕哈尔加姆恐袭事件引发印巴冲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成功斡旋停火,导致美印关系紧张,严重削弱了这一叙事的效力。美印关税战造成多个行业就业岗位减少,贸易谈判破裂与签证政策收紧进一步戳破了印度在全球顺利崛起的幻想。对于长期被自称为“全球崛起”与“世界导师”自我宣传话语激励的印度中产阶级与媒体而言,现实政治的冷峻逻辑正在逐渐冲淡其热情,并削弱先前的胜利主义情绪。
印人党在农村选民及城市贫困阶层中仍然保持显著的政治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其构建的直接福利转移体系。诸如“总理农村援助基金”、“简易账户”、“亲爱的姐妹关爱计划”等项目为民众提供可感知的物质收益。在经济不安全与普遍贫困的社会背景下,这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冲了公众的不满情绪,解释了为何即便印人党的霸权性政治架构已出现松动,其仍能在选举竞争中维持强势地位。然而,仅凭福利输送不足以长期支撑政治主导权。因此,印人党当局持续采取压制策略,打压异议、封禁反对派、监禁批评者、社会活动人士与知识分子,以巩固其政治秩序。
或许最无形却最具标志性的变化迹象是人民,尤其是反对派领导人,不再心怀恐惧。曾经,逮捕、骚扰与边缘化的威胁构成了印人党所依赖的治理生态,而这种恐怖氛围正在逐渐消解。反对派现在不仅展现出更强的协调性,同时也更具自信,能够主动开辟政治空间,并对政府形成持续性监督。诚然,挑战依旧存在,“印度国家发展包容联盟”仍需调和地区与意识形态差异。然而,反对派已不再是政府政策的被动批评者,而是积极塑造政治议程的主体力量。执政党长期主导地位中的裂痕愈加显现,尤其在议会层面表现突出。无论是在预算会期还是季风会期,愈加强势的反对派在多项政治与政策议题上正面挑战政府,使执政党陷入明显被动。以“古吉拉特模式”为代表的策略已难以奏效。一个更为团结的反对派已在种姓普查、“朱砂行动”、比哈尔选民名册特别修订计划以及选举舞弊指控等关键议题上对政府施压。
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由拉胡尔·甘地领导的国大党。他发起的“团结印度游行”成为关键转折点,不仅改变了其个人政治轨迹,也为国大党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印人党在2024年大选前夕冻结了国大党的银行账户,试图使其陷入瘫痪,但国大党依然重新积聚动能。此举适得其反,不仅未能削弱国大党的运作,反而揭示了印人党政府的高压手段,削弱了其长期营造的“不可战胜”的政治光环。甘地及其同僚由此成功推动了国大党形象的重塑,使其从一个被动反应的在野党转变为更为积极主动、具备议程设定能力的政治力量。真正的考验仍在前方:如何将这一转变转化为持久的政治实践与实质性的选举收益。
印人党政府推动加强对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控制,正是其政治霸权走向衰落的典型标志。近期通过《首席选举专员及其他选举专员法案(2023)》,削弱司法监督、强化行政主导权的举措折射出深层次的不安。印人党已不再愿意依循既有规则运作,除非能够按照自身利益对其进行重塑。一个真正对自身权力具有充分自信的政府无需重写制度规则。恰恰是这种重塑规则的冲动,揭示出其统治所面临的控制危机——担忧其长期主导地位已不再稳固。
或许对政权最具破坏性的进展是国大党领导的针对政府系统性操纵选民名单的指控。这原本可能被视为日常行政层面的纰漏,如今却被重新界定为蓄意破坏民主选择的策略。通过揭露大规模删除、仓促修改和针对反对派人口的算法模式,该运动将原本的技术性争议上升为对政权整体诚信的深刻质疑。这些指控不仅挑战了个别选举的公正性,更直指印人党政权胜利的合法性,暗示其政治优势并非多数民意的真正体现,而是源自对选举过程的结构性操控。
一个重要的比较是,印人党当前的执政地位常被拿来与独立后国大党的长期执政相提并论。但这种类比实际上掩盖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国大党的政治霸权不仅依赖于选举胜利,更在于其能够吸纳并反映印度社会在阶层、地域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力量。即便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其统治仍以某种广泛的共识为基础。相比之下,印人党的主导地位更多建立在社会分化与排斥之上股票配资线上,而非包容与调和。其权力的核心支撑主要来自选举胜利及对国家机器的运用,而非深厚的社会合法性积累。一旦这种机器失灵,裂缝便会显现。
证配所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